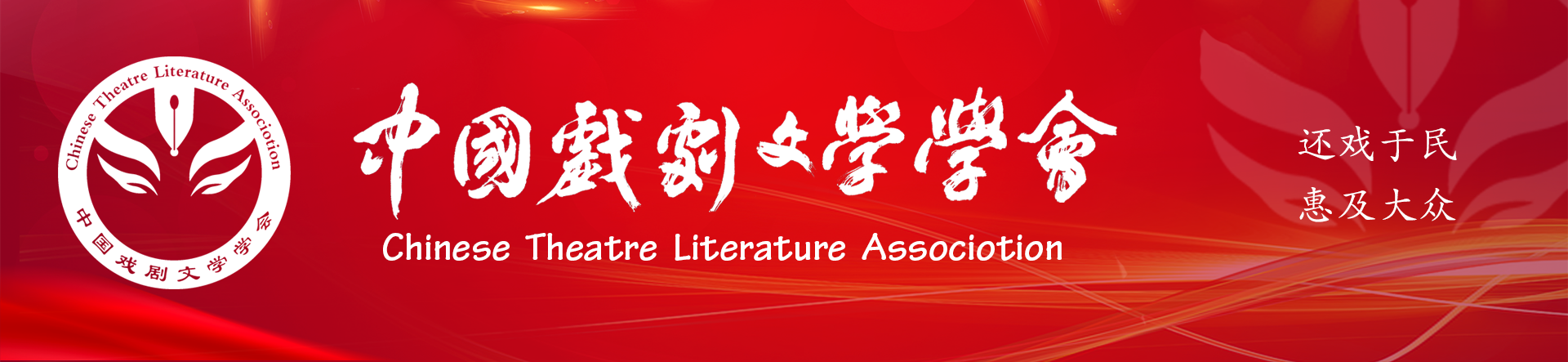话剧创作:关注当代人精神内省的痛苦
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当下的话剧创作明显滞后,处于令人尴尬的境地,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诸如创作观念落后、开掘生活不深、文学底蕴不厚、人物形象不新、缺少时代的前瞻性和艺术审美的震撼力等等。这与呼唤经典巨制、精品力作的时代要求相去甚远,实在令剧作家们坐立不安。好在话剧创作与审美的群体性,给话剧舞台注入了多种艺术兴奋剂,使之勉强支撑着漂亮却空壳的躯体,人们从导演的花样翻新、演员的精彩表演和舞美的高新技术中还是感受到了话剧特有的魅力,给予阵阵喝彩,话剧事业于是照样辉煌,话剧人照样频频获奖,频频举杯,煞是热闹。但是,热闹过后,却没有给人留下太多文学的历史的印迹,话剧文本创作的先天性贫弱依然令人困惑。为什么在今天社会急剧变革、经济迅猛发展的丰年盛世,却产生不了与之相适应的伟大剧作。从事话剧艺术的有识之士,包括剧作家、评论家,甚至主管话剧艺术生产的领导开始为其寻找病因,开具药方,从话剧创作的各个方面探究原因。平心而论,其中不乏深刻的剖析和真知灼见。其实,话剧文本的贫弱,有诸多的原因,影视艺术界“导演中心”的运作模式也在挤压话剧创作的文学空间。
我实在同意这样的观点:编剧与导演,同行不同道。编剧重文学的深入,导演重艺术的浅出;编剧重神,导演重形,二者有机结合,方能形神皆备。陈新伊的《徽州女人》由西递村的版画而起,装进了一个缺乏文学底蕴的故事,田沁鑫的《生死场》巧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身段语言,演绎了一段没有新意的生生死死,戏剧文本成为了导演把玩导演手法的玩物。然而,中国戏曲是从汤显祖时代才开始有所谓的“导演”来说戏并规范舞台演出的,谁能说出关汉卿的《窦娥冤》的导演姓甚名谁;话剧的经典巨作《雷雨》、《茶馆》、《蔡文姬》也是和曹禺、老舍、郭沫若的名字写在一起的。
西方戏剧出现导演一职,也是在近现代,我们不知道古希腊悲剧《俄荻普斯王》是谁导演的,而诗人编剧索福克勒斯的名字,却永远记录在世界戏剧史册中,经历了二千五百年。无论是中国的经典话剧,还是传世至今的古希腊悲剧,其编剧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有着诗人的情感、气质、思维方式及其艺术表现。
我无意削弱当今导演在戏剧艺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和非凡的贡献,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甚至很超越。我只是想重点地说出话剧创作要摆脱今天的尴尬与困惑,必须百倍地注重剧本创作,这是“从无到有”的艰难工程,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特别是文学的艰难工程,非诗人不能完成,非诗人不能达到她的文学的高度与深度。话剧艺术是一种当众表演的舞台艺术,追求现场共鸣并且令人回味,现场共鸣,要求找到一个话剧与观众的共鸣点;令人回味则要求话剧应有相当的文学性,此二者的核心是:人物。本文试图就其一点,谈谈话剧创作与当代人精神内省的“痛苦”。
生存状态与精神内省的多元形态
话剧艺术是最接近生活形态的艺术样式,话剧创作往往认为反映一般人的生存状态便是贴近生活,便是生活气息,但人物的喜怒哀乐总是显得浮光掠影,没有很好地展现出人的精神内省的过程及实质。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和语言,当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欲望发生冲突的时候,人就有了精神内省,这种内省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其过程便会是一种“痛苦”。可以说,话剧通常就是通过深入揭示人的“痛苦”而完成艺术创作与审美的全过程的。悲剧因为痛苦而崇高,喜剧因为无奈而痛苦。中国的抗战话剧是因为击痛了中国人将成为“亡国奴”的痛苦,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话剧是因为深深击痛了被“四人帮”压抑迫害的痛苦,《红楼梦》和《雷雨》都是因为揭示了一个黑暗腐朽的时代行将灭亡的时候,给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些正与人们的生存状态及精神内省的“痛苦”产生了共鸣,并且预示了人的共同的渴望、希冀与理想。再者,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既动荡又僵滞不前,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内省在同一社会条件下基本趋同,一部触动人的精神欲望的话剧,很快就会引起观众的共鸣。
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追赶世界先进浪潮,在人类资源共享的条件下,乘着“后进优势”以数倍的速度向前发展。本来十年二十年完成的经济发展和观念更新,在几年甚至几天的时间内完成。优胜劣汰的残酷,先进落后的换位,明星大腕的天价,百万彩票的大诱惑,一日暴富,一夜成名,使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内省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暴富者过着有钱又有闲的生活,用金钱掩盖着内心空虚的痛苦;失业的算计着明天的生活,用愤愤不平来诉说着他们的精神痛苦;明星们用头上的光环,遮挡着失去自由的痛苦;老总们在谈判桌上强装笑脸,深藏着恐惧破产的痛苦。凡此种种,于是话剧创作及审美价值的多元化现象也随之形成。但遗憾的是,这种多元化的创作只是停留在人的生存状态上,对人的精神内省的开掘尚嫌笔力不足,即使有些话剧精品触及了人的精神世界,但由于对当代人在认知上的超越与落差,或前卫,或陈旧,过于把玩艺术,没有能够重重地敲打人的精神内省的痛苦,难以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只能是有震无撼。
俗话说,艺术创作“贵在发现”,不在技巧。成熟的剧作家大都具有娴熟的剧作技巧,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把话剧当作“诗人之作”,当作“文学之品”,那么,如何提高对当代人的认知的深度、厚度、力度就应当成为话剧创作的首要任务,任何前卫性的超越与陈旧感的落差,都将不能与当代人产生精神共鸣,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部戏的命运。
行为动作与人性欲望的无限冲突
当代人所经受的精神内省的“痛苦”是前所未有的。二十年来,社会发展的急剧变革非正常运行,我们叫做“转型期”,经济的转型有赖于体制的变革,而各种价值观念的更替、易位却有赖于人的精神内省。当代人的精神承受着传统与现实、习惯与创新、拥有与失落的挤压,行为动作与人性欲望的无限冲突撞击成精神内省的“痛苦”,话剧创作应该去发现和表现这种痛苦,这是剧作家的任务。英国文艺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在谈到莎士比亚的卓越成就时指出:“除了人性的表现之外,确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悦众多的人,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人长久喜爱。”
长期以来,对当代人的认知,对戏剧人物的分析,我们曾习惯于运用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道德的认知方法,对人物作出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忽略了人性欲望在人物行为中的根本原动力作用,这是戏剧的“教化”功能在起作用,同时伴有领导意志、作家利益、社会功用等等。但是戏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告诉我们,只有人性欲望与行为观念的无限冲突,才能真正表现人物精神内省的最大张力。因为人性欲望是人物行动的原动力,是产生一系列人物动作的戏剧性本源,是对人的意志、情感、思想的催生剂,如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所说:“如果说我们所遭受的全部痛苦,所蒙受的一切侮辱,都只是在我们的脑海中产生滋长的话,那显然就不可能有所行动,更谈不上有英雄的行动了。”戏剧不必去解释这人性欲望究竟是什么,作为人物行为观念的原动力,只有当人性欲望的不断膨胀,其行为动作的不断调整,最后才能在文学的层面上完成人物的性格创造。从哈姆雷特、繁漪、王利发等人物的行为动作中,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人物的复仇、求爱和求生的欲望,如果没有了这种欲望的表现,而只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从“教化”的功能去创造人物,话剧作品的伟大和经典又何从谈起。
摆脱教化、宣传、获奖、名利等社会的功利性,摆脱剧作家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摆脱创作观念的混沌和迎合观众的市民意识,真正从话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出发,在人性欲望与行为观念的无限冲突中,揭示当代人精神内省的痛苦,才是剧作家走向文学的健康之路,才能真正赢得当代人的情感共鸣,满足他们的审美理想,使话剧艺术创作的现场共鸣不至于和电视娱乐混为一谈,赢得更大的观众层面。
情感本源与审美理想的心理落差
精神内省的痛苦与人性欲望的表现,都必须诉诸人物的情感表达,这是观众接受人物精神内省和人性欲望的唯一途径,而情感的表达方式又取决于人物的性格因素。剧作家塑造人物性格,将人物的行动和语言通过人物情感的渲泄或抵制传达给观众,激起观众同情、憎恶、怜爱、愤怒、惊恐、激昂,使之产生共鸣,这也是话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但是人物的情感本源究竟是什么,是思想,是意志,还是性格。目前话剧创作把人的情感本源放置在思想道德上,舞台上出现了许多与生俱来的英雄模范、灰色商人、流氓市侩。他们被放置在剧作家设定好的道德规范中,接受着社会一般化的检验和批判,甚至我们的演员、导演、评论家和主管戏剧的领导也是用这社会化的思想道德标准来评判戏剧人物的真实与否。这些人物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失去了剧作家的文学追求,舞台上的戏剧人物只有观众熟悉的生存状态,只有高尚美好或卑鄙恶劣的思想道德行为,却没有精神内省的痛苦和人性欲望的情感表达,他们是某种思想道德的戏剧符号,其精神内省与人性欲望的深刻性与文学性被庸俗化、简单化、功利化了。这样的戏剧人物是不可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理想的,他们看不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喜悦、惊恐、欢乐、愤怒、希冀和理想在舞台上的充分展示,找不到他们所希望的情感的释放和人生的启迪,更谈不上内心情感被艺术力量所震撼的愉悦。如果说话剧表现当代人精神内省的痛苦和人性欲望具有悲剧性的话,我们可以引用尤金·奥尼尔的一段话:“我认为悲剧的意义就是像希腊人所理解的那样,悲剧使他们变得高尚,悲剧赋予他们对事物深刻的精神感受,摆脱日常生活琐碎的贪欲。当他们看到舞台上的悲剧时,他们感到仿佛是把他们自己毫无希望的希望体现在艺术中。”
当然,剧作家的创作也许会有各种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干扰,比如有政治标准的衡量、社会道德的评判、领导意图的限制、参赛获奖的无奈、职称名利的诱惑。但是,剧作家的创作观念、文学修养、人生体味以及对当代人的认知水平也未必不是当前话剧创作提高艺术质量的障碍。由于话剧创作只在思想道德水平上塑造戏剧人物,情感表达不能深入到人的精神内省和人性欲望的本源,与当代人产生了严重的
落差,那么,当代观众的审美理想也必然与话剧艺术创作产生了心理落差。他们认为舞台上的人物还不如自己深刻复杂,他们嘲笑剧作家的肤浅和幼稚,他们无法得到审美的心理满足。不过,他们也曾经被舞台上的眼泪打动过,被戏剧性的笑料逗笑过,但回头一想,还不如回家看电视,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戏剧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没有能看到戏剧那近似于宗教的精神理想,没有感悟到话剧比电视更加给人以快感。这种让当代剧作家感到十分可怕的心理落差,使话剧在当代人面前显得十分尴尬,十分落伍,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
话剧创作,应当十分关注当代人的审美理想,关注话剧的文本性创作,关注当代人精神内省的痛苦和人性欲望的情感表达,让话剧的文本创作真正深入到文学的本源,使话剧艺术与当代人产生精神内省的共鸣,产生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当然,话剧创作如何走出困境,要关注的东西很多,本文只能就其一点发表议论,就教于同仁。
(高龙民:国家一级编剧,原载《上海戏剧》2003年第2期、《剧影月报》2003年第1期)